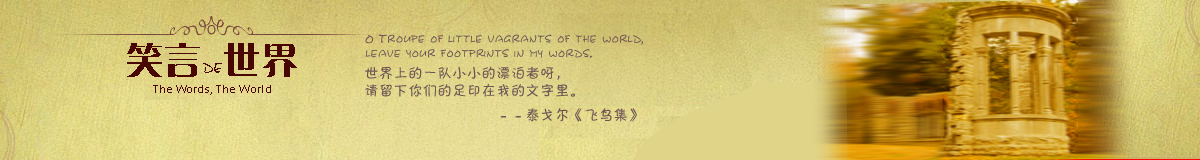笑言
笑言你个衰仔!还不把书写出来,要等着老子见上帝才出版吗?
佛生气哼哼地说着,大口喘着气,感觉肺叶像风箱门一样扇动着,仿佛陈年的木屑和灰尘在这一刻蓬然而起,弥漫了他的整个胸腔。
年轻时在木材厂剖木板,电锯前面一站就是一天,每天收工都觉得嗓子眼里有痰,吐又吐不出来,咳也咳不干净,难受得像吞了一只青蛙。
老板倒是丢给他一只口罩,但那口罩显然挡不住漫天的细碎木屑粉末。晚上回去洗澡,浓密的头发中嵌满了木粉,怎么冲都冲不干净,总是散发出淡淡的橡木味。后来他发现其实鼻孔里还残留了那个气味,于是洗澡便多了一道洗鼻孔的步骤。
干什么事都要有步骤。就像他小叔爷开的洗衣店,收来的衣服,先要检查兜里有没有东西,再抖干净浮土,然后分门别类泡进不同的水桶中。洗涤和熨烫那都是后来才做的。他小叔爷和堂叔管洗衣服,他管提个篮子去送货收货,当然有空他也帮着洗些小物件。那年他十二岁,个子矮,还够不着洗衣台,脚下要垫个木箱。洗一通袜子短裤,小脸累得红彤彤的,小手也泡得红彤彤的。
不过个矮也有好处,晚上就睡在熨衣台上,不用另搭床铺。
小叔爷待他不错,就跟对亲孙子似的。哦,其实他小叔爷眼下是他法律上的亲爹,他堂叔变成了他哥,因为他是顶替小叔爷小儿子虾球的名义过来的。虾球比他大三岁却比他大了一辈,还在佛生三岁懵懵懂懂的时候,虾球就在河塘里捉虾给淹死了。
佛生十一岁这年,久无音信的小叔爷来了封信,说加拿大废除了排华法案,他要回乡探亲了。
小叔爷四十大几,回老家想接叔奶去加拿大。可叔奶说国外太苦,办出去要花很多钱,而且去了还说不来洋话,所以不肯去。小叔爷嘴笨,说不了两句话就急得额头青筋暴起。他反反复复说加拿大限制华人入境二十四年,如今好不容易允许亲人团聚。谁知道错过这次机会,以后又会有什么法令。多次劝说无果,小叔爷的脸色铁青却又无可奈何,他常常一个人点支烟望着远处富庶人家的碉楼发呆。佛生顽皮,有时候忍不住过去逗弄他一下,这时小叔爷的眼睛会亮一下,或许是想起了自己早夭的小儿子。

临走的时候,小叔爷对佛生父母说,毕竟加拿大那边能赚钱,不如让佛生顶了虾球的名字过去,也能在店里搭把手。
在四邑这地界,人们都盼着出国发财回来给家里盖碉楼。有了小叔爷这句话,佛生爹妈二话不说就去凑钱了。
一年之后爷孙变父子,佛生来到了加拿大。小叔爷把他安排进华人教会的中文学校学英语,这学校晚上上课不耽误白天干活。佛生很快跟华人孩子们打成了一片,上学、做礼拜、出去玩都在一起。等英语能勉强交流了,小叔爷把他送进了本地学校。学校上课时间不长,放学回家后还能干不少活。
佛生这样的人,叫做买纸人,就是说花钱买了一张移民纸。他是纸儿,小叔爷是纸爹,堂叔是纸哥。纸哥的话不少,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。纸爹和纸哥有个习惯,他们搛菜之前,喜欢把筷子在木质的桌面上咄咄地跺几下跺齐。一顿饭,纸哥的话就在这咄咄声的间隙中不停地响起。不过他翻来覆去总是抱怨洗衣没出息,看人家黄家的餐馆生意有多火爆,连总理都去吃饭。
纸爹冷不丁会撂下一句:你洗的也是总理的衬衫,还有总督家的桌布呢。在佛生眼里,纸爹沉默得就像一座碉楼,别人不去搭话他可以几天不讲话。
一晃两年,纸哥跟别人合伙开饭店去了,佛生成了洗衣店中里里外外一把手。遇到给名人们熨衬衫的时候,他总要去插一脚,含一口水,噗地喷上去,纸爹的熨斗滋地掠过,两人配合默契,天衣无缝。回家看望父亲的纸哥在一旁黑着脸说,报上都说了,华人洗衣店不卫生,口水到处喷。佛生哈哈笑着说,就是要让大人物们沾沾我的口水。
暑假的时候,佛生从早忙到晚。一天傍晚他接到客户电话去取脏衣服,来到一个看上去挺气派的平房,按了门铃。里面说:进来!
佛生推门进去,又听里面说:往里走!他来到卧室门口就愣住了,大床上摞着两个人,那男人指指地毯上的一堆衣物。佛生赶紧拿起来装进篮子跑了出去。身后传来一阵放肆的笑声。
送回洗好的衣服时,只有男人在家。那人瞅了他一眼,问:小中国佬,你在洗衣店一天赚多少钱?
佛生不明所以,但还是说了一个数。
我给你两倍的工钱,你来帮我干一个月。
佛生想了想说:我爹还管吃住呢,你管吗?
管一顿饭,不管住。这样,我给你三倍的工钱,你干不干?
干!说完佛生才想起来问,我去干什么?
男人说:去木材厂。有个笨蛋砍伤了自己的脚,我缺个帮手。
佛生回去告诉了纸爹这件事,说下工回来自己还能帮家里干活。纸爹看他一眼,点点头说:去吧。接着他转过身叹了一句:靠洗袜子,盖不起碉楼啊。然后他便又变成了沉默的碉楼。夜深了,那座碉楼缓缓移动到外面的门廊坐下来。只有那一明一暗的烟头,才让人知道那不是碉楼。
佛生有点莫名其妙的忧伤,他舍不得离开小叔爷。不过他明白木材厂那份工是临时的,等那个白人小伙子养好伤回来,他就得滚蛋。木材厂这么好的行业,华人是不能染指的。要不是救急,要不是工钱便宜,老板也不会找上他。
佛生在木材厂干了两个多月直到假期结束,小赚了一笔。高中毕业后,他还是离开了洗衣店,用积攒的钱和中文学校认识的小伙伴在郊外买了一个小农场,专门种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。几年下来,他跟唐人街餐馆和日杂店的老板们混得很熟。
过春节的时候,佛生照例去老人院看望了纸爹。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老人,独自坐在窗前凝视着天空发呆,似乎那里有什么遥远的东西,值得他花一生的时间去张望。佛生看着他碉楼般凝重的背影,忽然想起小叔爷回到家乡的那一年,他也是这般抬头呆望,心里遗憾自己没能力给家里建一座碉楼,嘴上却什么都不说。
佛生走近老人,轻声说:小叔爷,老家富裕了,也不建碉楼了,您不用为他们操心了。老人浑身一震,从把佛生接来那一年起,他就让佛生改口管他叫爹。白云苍狗、沧海桑田,几十年了,佛生还是第一次改正了称呼。
小叔爷抓住他的手说:好!好孩子。不管你叫啥,我们都是一家人。
我是佛生,也是虾球。佛生用另一只手覆在了那双苍松般的手上。
听说你想盘下唐人街那个地毯商店?老人忽然问。
啊?这您都知道了?佛生说,这才没几天的事。
老兄弟们告诉我的。小叔爷说着取过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支票递给他说,知道你钱不够,我给你加点。
佛生没废话,直接收了下来。他对老人说:我要开一间唐人街最大的华人超市。赚了钱孝敬您。
小叔爷摇摇头说:我要钱没用了。在这个安静的房子里,我时常能听到召唤声,是天国的声音。
佛生不但赚了钱,还成了华商会的风云人物。在一次慈善募捐的高尔夫球活动中,他认识了一个叫笑言的华人作家。作家跟他聊了几次,又打球又喝咖啡又吃饭。可是等把他的故事掏干净了,作家就没影了。说好的把他的经历写成励志故事,他却一直没等到。如今连他自己都住进了老人公寓,他等的书还没有出版。
佛生很生气,身体一不舒服就骂那个作家几句。

——写在《一座世纪牌楼的诞生——历史长河中的渥太华华人》(笑言编著)出版之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