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笑言
非常荣幸在加中笔会成立25周年云庆典上,有机会与各位分享一点写作体会。
非虚构文学创作中,真实是第一位的,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想象力是受到制约的。那么在非虚构写作中,是不是我们只能写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读到的?那么我们听来的、读来的,就一定是某个事件、某段历史的真实吗?有些时候,作者要为尊者讳;有些时候,要顾及民族感情;有些时候,要尊重宗教信仰;有些时候,要注意政治正确,那么严肃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,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,还留给作者多大的想象空间呢?
我个人以为空间不大。有人把非虚构写作分为Critical nonfiction和Creative nonfiction,即严格非虚构与创造性非虚构。作为写作人,我们对创造性非虚构当然更感兴趣。简单说,创造性非虚构就是要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边界相融合。写作基于一个事实或一个人物,同时引入小说、戏剧的种种元素,比如场景设置、语言音调、角色塑造、蒙太奇切换等等。
我写渥太华华人历史的第一篇短文,题目叫做《孤独的汤姆墓》。渥太华向南56公里,有一个小镇叫坎普特维尔(Kemptville)。这个镇子边上有一大片墓地,称为坎普特维尔公墓,又叫联合墓地,里面密密麻麻竖满了墓碑。这种景象在加拿大司空见惯,但这里与众不同的是:有一座墓碑极其醒目地远离整个墓群,独自伫立在旷野上,墓群中离它最近的墓碑也有百米以上。
墓碑上简单地写着:TOM CHU, CHINA, 1873–1948。译成中文就是:朱汤姆,中国,1873-1948。出生地简单到只有“中国”两字。墓碑已从接近地面处断裂,所幸被人在两侧用两块钢板固定了起来。
这就是基本的事实。看到这样的场景,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产生了解的冲动,写作的冲动。那么,怎样去表现它呢?当然首先需要搜集资料。需要明确的是,非虚构写作从来不等同于客观写作。作者带有自己的倾向与情感,读者也会带着自己的观点去参与作者的记述与想象。相对严格的非虚构写作中,非常重要的一点,就是要让读者看清作者在事实与想象之间的切换。真实事件结束的时候,往往就是想象的开始。事实上,想象可以看作真实缺失的部分。想象为真实添加了活力、层次和深度。我们常常会用“假如……”或者“我想……”这样的句式开头,以界定事实与想象的分野。
一座孤坟遥对一片墓群的奇特景象,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。1996年,渥太华的一份小报提到有一位华人被安葬在坎普特维尔镇公墓,但该墓远离墓群,墓碑断裂,无人照料,更无人知晓墓主的生平。当时在安省卫生部工作的周树邦先生偶然读到这则消息,心绪难平,很想了解这位前辈何以为生,曾经遭受过怎样的磨难,又获得过怎样的成功。周先生和亲友们曾多次借踏青的机会凭吊汤姆墓。近20年之后,周老先生向我提供了这条线索,希望我能解开他心中长久的疑问。
你看,仅仅这样一座特殊设定的孤坟,就引发出如此多的联想与缅怀,甚至愤怒的情绪。作为一名作者,我们的想象只会更多,探求真相的愿望也只会更强烈。
2012年春天,一位来自蒙特利尔的园林工人马丁(Martin Gregory)在坎普特维尔工作时见到了这座孤坟,感到十分震惊。他上网发了一篇短文,文中充满了对墓主的好奇。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?汤姆的墓葬与主墓群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隔离?汤姆是小镇唯一的中国人吗?加拿大和美国那么多拥有华人社区的城市,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小镇?他生前从事什么职业?他在这里有亲人吗?如果有,为什么墓碑上的出生地仅仅只写“中国”两个字?如果没有亲人,那又是谁为他下的葬呢?把他葬那么远,是对华人的歧视还是另有原因?
接触马丁的同时,我认识了拥有艺术史学位的作家伊尔琳(Earleen)。她说,从符号象征学来看,墓碑上半部圆圈内向上指的手,显然意味着“通向天国”。汤姆1948年去世,但石碑却呈现出更早的年代特征,不是1948年应有的风格。伊尔琳因此推断这是一块19世纪“剩余的”碑石,汤姆去世时,被人顺手拿来做了他的墓碑。这就是基于事实、基于细节、基于学识的合理推论,也是一种想象。
非虚构写作中,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,走访当事人、目击者或他们的后代。这些史料固然非常珍贵,但它们往往是孤立的、互不相关的、语焉不详的。想要将这些事件连接起来,很大程度上需要作者的想象。可以说,写出来的所谓真相,其实是作者对事实梳理后想象出的一个版本。
我在加拿大政府的人口普查网上,从1825年到1916年,输入各种查询条件,均未查到汤姆的记录。于是我直接给汤姆墓所在的安大略省家谱学会利兹与格伦维尔分会(Leeds and Grenville Branch)写信询问。该会研究所的切斯特(Len Chester)先生给我回了一封长信。信中说家谱在近代包括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二的记录特别差,这是因为许多纪录由于隐私的缘故被关闭。汤姆那个年代华人姓名的英语翻译非常糟糕,汤姆是一个用于英文场合的名字,登记在册的恐怕是他的中国姓名。切斯特先生也查了当年的人口普查以及选民名单,但都没有找到汤姆,当然很可能汤姆那时根本没有选举权。
在历史事件的写作过程中,特别是当写作对象鲜为人知、或者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线索时,作者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。我们既不能脱离事实,胡编乱造,可也不愿意写出干巴巴的文字。作品的可读性与诚实性就出现了矛盾。
有些作家建议用模糊的手法来处理,常用的句式是:“也许他会这样”,“也许他会那样”……
但这要有个度。时间关系,我也不举例子了,好作品很多,比如李彦老师的《不远万里》(Faith Fears No Distance),比如张翎老师编剧的新电影《只有云知道》,比如早年轰动全国的徐迟写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比如Daniel Brown写的The Boys in the Boat(《船上的男孩》),还有渥太华华裔女作家Denise Chong(郑霭玲)写的Lives of the Family – Stories of Fate and Circumstance(《家庭生活》)。
我个人感觉至少对于严格非虚构作品来讲,更像做学术研究。如果想象的成分太多,就会超越真实的边界。有些想象的情节,适合于小说,但不应该出现在历史的记述中。
与汤姆墓一路之隔,Dairy Barn快餐店的店主玛利亚时常给汤姆墓送上鲜花。我采访她时问及原因,她说只是看着一块孤零零的墓碑立在那里心里不好受。好朴素的回答,让人心暖。那么这样的细节我觉得是可以扩展的,你可以写一位本地人站在汤姆墓前的感慨,也可以把采访中不曾提到的花卉、天气等等,根据你设定的情境,加以文学的描述,用逼真的细节去补充真实的细节。生动的细节可以产生画面感,逼真的补充可以给角色添加血肉。如何运用自己和他人的经验,以及想象力弥补现实材料的不足,是写作的乐趣之一。
观察力和想象力是作家必备的要素,我觉得写作时产生的想象是自然而然的,与经验有关、与长期的写作训练有关、与审美的偏爱有关。想象与经验密不可分,不同的亲身体验和间接经验赋予我们不同的想象力。也因此,作家才能给自己的作品打上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烙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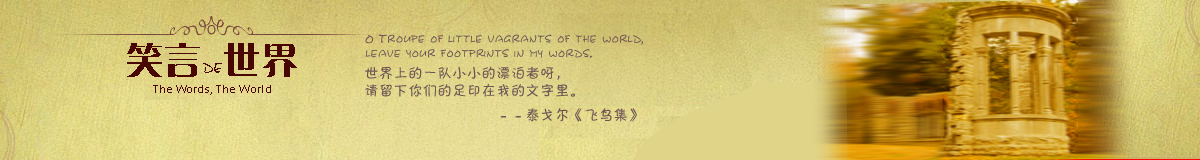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
要发表评论,您必须先登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