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笑言
小说《围城》有一段关于牛津剑桥师生共同吃饭的精彩描述,其中教育部视学先生的口头禅“兄弟在英国的时候……”更是广为流传,甚至沿用至今,成为某些“海归”最传神的简笔勾勒。我不能免俗,这篇文章就这样开头吧:兄弟在牛津的时候,和老师同学一起吃饭,前后“共同”了两年。

牛津大学实行院、系并行的独特体制,新生入学,必须同时选择一个系和一个学院。系负责安排专业课程,于是便有一个专业导师(Supervisor)。学院负责吃喝拉撒睡,于是便有一个德育导师(Moral Tutor)。德育导师不训话不布置作业也不主动做学生的思想工作,学生和专业导师之间发生矛盾,或遇到特殊困难,可以向德育导师寻求帮助。不过,学生和学校的矛盾通常不会大到要真的动用德育导师,于是他们的任务便简化为每学期(牛津一学年分三个学期)请自己名下的学生吃一两次“高桌子(High Table)”。
所谓High Table,就是放在餐厅主席台上的一排餐桌,就餐时学院的头头脑脑和教师轮流坐在上面值班,再就是被教师请去的学生。说是请在一桌吃饭,其实还是分餐制,一人一份,各吃各的。去高桌吃饭还有个规矩,就是要穿无袖的黑袍(Gown)。每个周末总有一两个学生被请上去吃饭,也就是说,每个周末都有十几个教师,一两个学生在高桌上吃饭,其他学生则在下面的两排纵向拼在一起的长桌子上用餐。
牛津学生的衣橱里,不管缺什么,一定不会没有黑袍,它是吃饭和考试都少不了的道具。不过平日吃饭用不着,只要拿一张饭票,就可以换一盘汤、一道主菜、一碟水果或甜点。
周末伙食好一点,便需两张饭票,还必须穿上黑袍。吃饭与考试不同之处是可以不戴那顶正方形硬顶带穗的帽子。餐厅里零星几位没穿黑袍的,必是请来的外人。高桌上的客人齐了之后,某位老先生,十有八九是学院的院长,便会用力敲一下法官手中那样的木槌(Gavel)。随着这惊天动地的一击,不但上面的高桌,下面的几十张桌子也一齐安静下来,听他用拉丁文高声做餐前祈祷。言毕就坐,餐厅的十几盏大吊灯随即熄灭,只余下紧贴天花板的反射辅光灯还亮着。蜡焰如星星之火,在每一张餐桌上跳跃,大家开始集体烛光晚餐。
一旦被德育导师请到高桌上去,就免去了那两张饭票,同时还会发现高桌上的食物原来比两张饭票所能买到的还要丰盛。侍者会躬身轻问,先生喜欢喝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?
除了德育导师,专业导师也有请学生吃饭的义务,且专款专用,学生的大餐绝对跑不掉。我经历中最隆重的一次是专业导师邀我参加圣诞晚宴。那顿饭要我自己掏钱断不会去,餐费远不是两张饭票可以打住的。
夕阳还没有落下,晚宴就开始了。学院的餐厅在后院,餐前酒却安排到前院的南楼。当时正值一位教师在那里举办个人画展,于是大家三三两两端着雪利酒或聊天或品画,特有的英式幽默在轻笑中如空气般流动着。
那天的我不仅披了黑袍,而且西装革履,打了白领结,完全是入学照集体像时的规格。
餐厅所有的桌子都铺上了洁白的桌布,整齐地摆放着就餐者的名牌和一份白底银字封面的菜谱。落坐后才发现我的黑西服根本算不上隆重,教师们几乎全都穿着丝光长翻领的短礼服,高桌那边则是清一色的燕尾服,就像一群乐团指挥围着一架巨大的钢琴在开会。我对面坐着的一位夫人穿了袒胸露肩的晚装,戴着一顶饰有黑网眼纱的帽子。我忽然有些恍惚,仿佛走进了某一部电影。木槌敲过之后,大厅暗下来,桌上一簇簇温暖的烛光将餐具映得熠熠闪亮。小竹筐端上来,里面盛满橄榄状的小面包。我取了一个,用刀从中间剖开,却不切透,再涂上黄油,用手掰着吃。这些规矩都是洋人点点滴滴从小慢慢吃出来的,我们小时候喝的是稀饭吃的是面条,吸溜的声音越响表示吃得越香。而到了国外,尤其是上了牛津的高桌,却是不能发出任何声响的。这种文化习俗上的差异往往派生出非常经典的小故事,我的一位好友刚出国第一次去跟导师吃大餐,吃完一个面包觉得没饱,看看筐里还有,就又吃了一个。还饿,再看,还有,再吃。如是者三,终于小饱。小饱之后,他才发现源源不断端上桌的还有汤、牛排、色拉和甜点……
我们圣爱德蒙大厅学院的大餐是有名的。忘记什么时候看过一篇中国校友写的文章,说去圣爱德蒙大厅学院吃饭,侍者是半跪着上菜的。实际的情形是侍者端一硕大的托盘照顾一桌的客人,通常要把托盘架在肩上,走到客人身后,屈一腿,躬身,请就餐者取用。
时间长了,那顿饭到底吃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,西餐吃的也就是一个气氛。还有印象的是阿拉斯加冰激凌大饼,热腾腾的大饼与冰激凌配在一起造就了奇妙的美味。好像一共上了四道菜,两次葡萄酒,第二次我对侍者说不喝了谢谢。不料过了一会,她又转回来问,先生要不要来杯果汁?她们的态度总是好得出奇,记得有一次我打碎一只玻璃杯,一名女侍立刻跑出来收拾,还一再问我要不要紧,倒像犯错的是她自己。
宴会上还有个小节目,就是拉圣诞礼物响炮。相邻的两人为一组,一人捏牢一头,用力一拉,“啪”地一声,拉炮炸响,一分为二,小礼物落在谁的一端就归谁。我那天运气不坏,拉到一副袖珍象棋,后来机缘凑巧,请世界冠军谢军在棋盘的背面签了名。
导师在宴会结束的时候匆匆赶过来要我等他一会。只见他飞快地在人群中穿梭,跟各色人等道着晚安。我的导师兼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,事务多,应酬也多。忙完后他领我走进后院的另一座小楼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宴席尚未完全结束,这里还有二十多人留下来喝咖啡呢。领座员问明谁和谁是一起来的,就立刻棒打鸳鸯,搞乱顺序,把不认识的人安排到相邻的座位。这样一来,每个人都必须跟陌生人交谈,社交圈子也就从理论上扩大了N倍。
后来搬了一次家,离学院远了,就不常去餐厅吃饭了。尤其是周末的晚上,我实在懒得多穿一件黑袍。当然,被请去坐High Table则另当别论。
英国人说,培养一个绅士需要四代人的努力。看他们把吃饭这件很平常的事情搞得如此庄重,才知道绅士的礼貌和风度原是这样来的。
往事如起纹的水一样渐渐模糊了,High Table却一直留在属于牛津的记忆中,定格为一份不褪色的怀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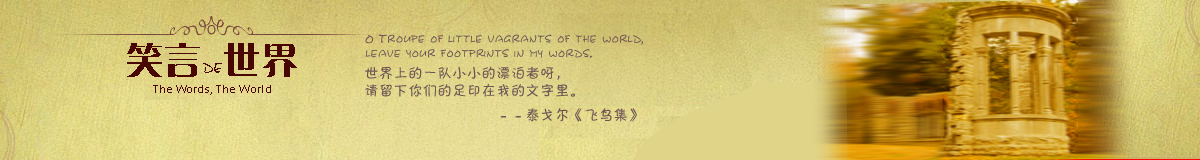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
要发表评论,您必须先登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