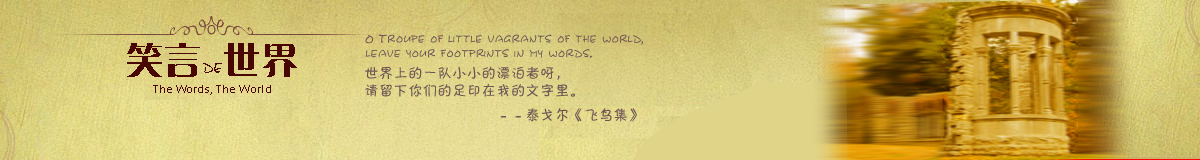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,对故土最具体的怀念莫过于饭菜。不一定是珍馐美味,也不一定人人都喜欢,只是自己从小吃惯的那种味道。
年轻时在国内,冬天的街边常有人摆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的火炉卖烤红薯。还未近前,浓烈的焦香味就扑面而来。红薯这东西,不同地方有不同叫法,有的叫番薯,有的叫地瓜,而在我的家乡就叫红薯,因为它的外皮是暗红色的。加拿大超市还有一种细小的紫皮品种,不那么甜但很密实,称作紫薯。
街边烤红薯比在家里烤香甜,这不是错觉而是烤炉的功劳。改装烤炉的人是个天才,废物利用妙到毫巅。大油桶下部砌出一个圆桶形炉膛烧炭火,也有烧蜂窝煤的,靠上的一圈台阶放红薯。桶顶开口加盖,以便火钳伸进去加煤以及取放和翻动红薯。而烤熟的红薯则放在桶顶的铁皮上,既保温,又是最好的展示。

家乡的红薯皮红瓤黄,口感甜糯,但就像去菜市场一样,再好的菜顾客们仍然免不了要挑拣一番。精明的摊主总是在烤炉顶盖上摆几只形状和颜色各不相同的红薯,有胖呼呼的、也有两头尖的、还有弯着腰的。围在炉边的买者以年轻女孩为多,很多小情侣也经常光顾。面对外焦里嫩流着焦褐色浓稠液汁的红薯,任谁都难以抗拒那巨大的诱惑,忍不住咽口水。
曾经听到排在前面的女孩艰难地说:你别再给我买了,我都吃胖了!随行的男孩笑着说:没的事,想吃就吃嘛!摊主则不失时机地推销道:你们是要吃甜的还是面的,还是要水大的?所谓“面”是家乡的表达方式,形容吃起来比较干噎,但有人就喜欢那种绵密的甜腻,哪种红薯更受欢迎因人而异,还真没定论。
棘手的事情我们通常形容为烫手山芋,英文中也有相应的说法叫烫土豆Hot Potato,其实应该叫烤红薯,因为它更有群众基础。离开烤炉,男孩女孩手中各捧一只滚烫的红薯。女孩手中的是细溜溜的,男孩手中的是圆滚滚的。他们捧着烤红薯在双手间不停地倒来倒去,嘴里喊着烫,手都顾不上拉了,两个人甜蜜得仿佛两只烤红薯。
买一个烤红薯,手暖、嘴暖、全身暖,最适合边走边吃。街边的烤红薯与冬天形成一道绝美的风景,那一个个动画般鲜活的场景至今还留在我记忆深处。有时也在家里烤红薯,但家里的烤红薯的确没法跟大油桶烤出来的比,因为家里的炉子烤不出红薯表面的那一层焦褐粘稠的硬层。那像是一层糖浆,最是香甜可口。大油桶烤的红薯可以在里面长时间加热,只要还没卖出去,就一直焖在炉子里面,焖得非常透、非常软,淀粉分解为麦芽糖,随着水分流失,糖分愈加浓缩,甜度自然更高。这是一般家庭炉灶难以做到的。
红薯是一种接地气的、介于主食与零食之间的食物。可以烤着吃、也可以蒸着或煮着吃,还可以煮在粥里做成红薯稀饭。从营养学的角度看,不论怎么烹饪,一个红薯所产生的热量是相同的。红薯富含膳食纤维,能润肠通便,吃下去还能增加饱腹感,因此被当作很好的减肥食物,但是它毕竟跟土豆差不多,也有相当多的热量,吃多了一样会胖。而且吃得太多,肚子里产气太多,会不时制造局部空气污染。
红薯这东西,在加拿大叫Sweet Potato。每当秋末冬初新红薯上市时,我总要去买上一些。加拿大炉子的烤箱很大,如果烤得时间足够长,也会“出糖”焖出焦汁。坐在一旁读书,甚至还能听到烤出焦汁的滋滋声。唯一不好的地方是,冬天不便开门窗,尽管开足油烟机,紧闭房间门,楼上楼下还是会充满惊天动地的烤红薯味。
烤红薯非常简单。洗净红薯,不包铝箔,直接放入烤箱,温度设定在华氏400度,烤一个小时即可。关火后最好再焖一会,端出来就是软软的、焦焦的、香香的、甜甜的烤红薯。趁热手忙脚乱地吃下,果然心满意足,觉得生活好奢侈,没有了年轻时摸摸口袋、看看烤红薯的犹豫与窘迫。
烤红薯解的不仅仅是嘴馋,这熟悉的味道一下就把我带回故乡。仿佛年少的我,又一次站在了街边的大油桶前。